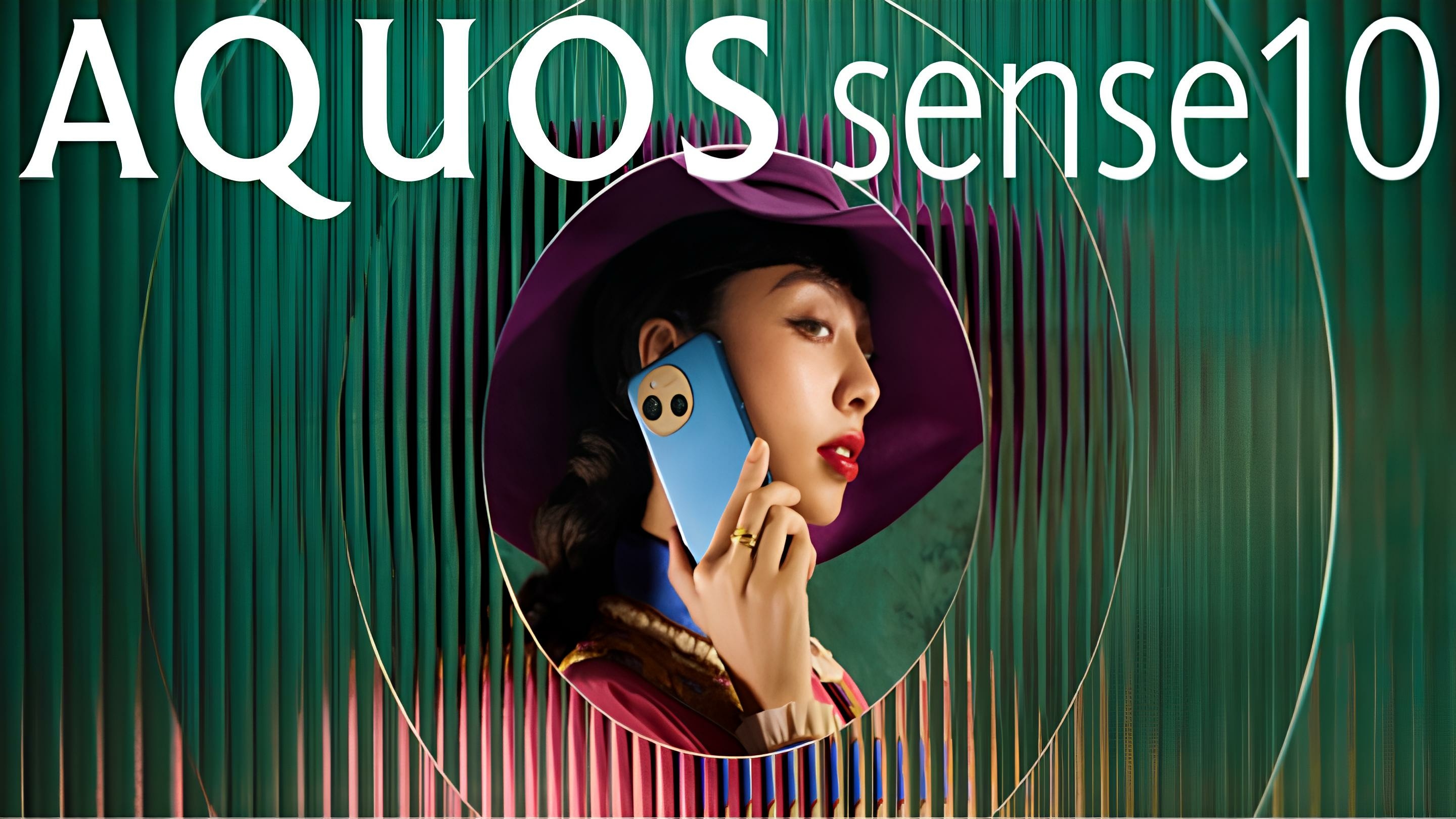中國是世界上龜類最豐富的國家,也是龜類最瀕危的國家。其中,中國斑鱉的故事耐人尋味。斑鱉體型非常大,壽命非常長,但也難逃瀕危的命運。

蘇州西園寺的斑鱉

Gerald_Kuchling博士在檢查長沙動物園的斑鱉
科學時報訊,如果問世界上哪種瀕危動物的數量最離奇,答案一定是斑鱉。
如果問中國目前哪種野生動物最瀕危,斑鱉肯定榜上有名——它是比中華鱘更瀕危的“水中大熊貓”——現在,全世界在人工飼養狀態下的斑鱉個體是5頭,其中中國4頭:蘇州西園寺2頭(一雌一雄),蘇州動物園1頭(雄性),長沙動物園1頭(雌性);還有1頭在越南的還劍湖。
事實上,“4”這個數字至今仍存在不確定性。“蘇州西園寺的居士們說西園寺有兩頭斑鱉,但我們只看到一只,雄性的。當然,他們說有並不代表就有,我們沒看到也不代表就沒有。”5月22日,WCS (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兩棲爬行動物項目協調員呂順清接受了《科學時報》記者的電話採訪。

馬來西亞鱉
增增減減: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前,中國斑鱉的數量曾經明確為5頭。
2005年10月,北京動物園的雌性斑鱉離世,距離它從“黿”正名為“斑鱉”僅一年。
2006年12月16日,在上海動物園兩棲爬蟲館內,一頭斑鱉始終未能得見任何同類,在遊客投擲的硬幣的包圍中,孤獨寂寥地終其一生。其時,距離為它“驗明正身”的“斑鱉保護蘇州研討會”不到3個月,這個研討會是由WCS等部門聯合召開的,主要討論如何將中國境內的4頭斑鱉集中養護起來,此前它常年被誤認為“黿”。
短短一年零兩個月,“5”減為“3”。
慶幸的是,時隔一個多月後,這個數字又恢復為“4”。
今年1月,WCS專門邀請澳大利亞西部大學的龜鱉動物繁殖生物學專家Gerald Kuchling教授來到蘇州,與有關部門就蘇州動物園和西園寺的斑鱉池改造設計進行論證。“此前中國動物園協會曾經發文給全國動物園,看是否有漏認斑鱉的情況。長沙動物園一位獸醫把自己園中飼養的‘黿’的照片傳給了蘇州動物園。從這組照片中,大家發現這只黿疑似斑鱉。隨即,Kuchling教授和我趕到長沙動物園,經鑒定,確認是斑鱉。”呂順清說。
“更讓人高興的是,它是雌性的,而且最近幾年還在產卵,給人工繁殖大大增加了希望。因為其他幾頭都是雄性。”
為什麼中國斑鱉的數量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一個重要原因,竟然是因為人類“不太認識”斑鱉。

鱉寶寶
冷冷清清:天下誰人不識君?
斑鱉曾廣泛分布在長江下遊、雲南南部紅河流域以及越南北部。從歷史記載中可以找到這些證據——
相傳清朝杭州藩司衙門門前有兩座石欄圍繞的大池,其中隱藏著藩庫的水門。看守水門的大黿就在池中,杭州人稱之為“癲頭黿”。這些傳說較難查證,但“藩司前看癩頭黿”,是杭州城裏市井中的一景,亙亙數十年不改。
曾生活在南京的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提到過斑鱉。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中,賈寶玉說:“明兒我掉在池子裏,教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王八,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
《清嘉錄‧楓橋倚棹錄》有一首《西園觀神黿》詩,記錄著“大黿”在西園寺放生池中自由自在生活的情景:九曲紅橋花影浮,西園池內碧如油。勸郎且莫投香餌,好看神黿自在遊。
但直到100多年前,斑鱉才慢慢被人類認識。
1873年,英國學者John Gray將駐上海的一個英國領事在上海附近捕獲的幾只大鱉定為新種,命名為斯氏鱉(Osaria swinhoei);除獲得一個博物館標本,經過十幾年的尋找,未發現任何一個斑鱉的野生種群。後來,學者梅爾蘭將斯氏鱉(Osaria swinhoei)更改為Rafetus swinhoei。1880年,法國人Heude又將在黃浦江抓到的大鱉定為一新種Yuen maculatus,並撰文指出新種與大黿迥然不同。但由于當時人們一直稱呼它為黿,所以他就入鄉隨俗將其叫做斑黿。據研究,Gray定名的斯氏鱉實際上就是Heude命名的斑黿。
1984年,中國學者張明華對浙江省桐鄉縣羅家角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黿骨骼亞化石進行了研究,定名為太湖黿。其實,太湖黿就是斑鱉,因為他當時沒有參考英、法學者的文獻。
前文提到的癩頭黿、大黿、斯氏鱉、斑黿、太湖黿都是斑鱉。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裏,我國學者幾乎無任何後續報道,甚至連它是否為有效種、它的地理分布和生活習性也一無所知,因而在我國鱉科動物分類上,曾一度呈現混亂局面——被認為是中華鱉的同物異名,雖然發現過不少個體,但都被鑒定為黿、斑黿等物種;中國所有動物園和博物館裏的斑鱉標本都被錯誤地鑒定為黿。
蘇州動物園為支持蘇州科技學院生物係建設,曾贈送了兩只俗稱“癩頭黿”的大黿標本。蘇州市科技學院生物係教授趙肯堂對其頭骨、背、腹甲等進行了細致研究,發現這兩只“癩頭黿”是斑鱉。經過多年研究,趙肯堂提出了大量證據,證明斑鱉是一個獨特的物種,是為斑鱉正名第一人。1992年起,趙肯堂多方奔走,為拯救斑鱉殫精竭慮。他的呼吁引起了反響,蘇州市民從此把斑鱉看做國寶。
WCS中國項目代表解焱介紹說,目前判斷斑鱉的主要依據有3個:一看體長,背甲長度達到80至110厘米或以上,但動物園昆蟲館的現有個體表現並不樂觀;二看體重,達到100至180公斤,可幼小的斑鱉個體和中華鱉、山瑞鱉等非常相似,因此很難區別;三看胼胝體,腹部有兩個。
如果說人類一直不認識斑鱉是斑鱉數量難以確定的重要原因,那其數量劇減的根本原因則是棲息地——太湖等地——遭到了污染等人為幹擾。而且,中國人向來喜歡進補龜鱉類,其中斑鱉個體大、目標顯著,更易被捕殺。

鱉池
對對錯錯:你的柔情我永遠不懂
漏認不要緊,關鍵是在人工飼養中,不懂斑鱉的生活習性容易讓斑鱉“折壽”。
“斑鱉本來喜歡吃什麼?吃多少?因為目前的斑鱉都是人工飼養很多年的,它們的習性或許已經改變,或者對人類投喂的食物產生了依賴性,很難抓著水裏的魚蝦。根據其他類似龜鱉的習性,應該喜歡吃魚蝦類。西園寺的斑鱉主要吃龜類,在水裏抓,在水裏吃。而曬背的時候,大家可能和平相處,就是網絡上流傳的‘百龜朝鱉’照片呈現的場面。”呂順清說。
“只要有太陽,斑鱉都要曬背。西園寺為了讓斑鱉曬背,用水泥造了一個人工小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野外狀態下,大型鱉類應該是在沙土性質的河岸上曬背。”呂順清說。
為什麼斑鱉需要曬背?“因為兩棲爬行動物都是冷血、變溫動物,體溫跟外界的溫度一樣。曬背能把它的體溫提高到一定程度,提高體內酶的活性。同時利用紫外線殺菌。”呂順清說。
“從當年的11月到來年的三四月,斑鱉每年要冬眠4到5個月,具體要視春天升溫快慢而定。”
“2004年底,北京動物園的黿被鑒定為斑鱉。但很多人不知道,甚至連北京動物園管理人員都不知道,還是把它當黿來養,最後斑鱉死掉還說這頭黿死掉了。我們不斷提供鑒定照片,才確定它真的是斑鱉。”解焱說。
“目前的飼養池塘和放生池均呈封閉式,斑鱉既缺乏登陸的路徑,也無攀登上岸之力,所以即使尚能生育產卵,鱉卵也無法在水中發育孵化。不難想象,在這樣的生存條件下,幾乎完全沒有可能使它們恢復到維持其保種數量的水平。”趙肯堂說。
呂順清也承認,在斑鱉的研究上,中國還有很多功課要補。
所以,WCS邀請Kuchling教授對蘇州動物園和西園寺的斑鱉池改造設計獻計獻策。實地勘察之後,Kuchling教授提出了很多改造意見:營造斑鱉上岸繁殖所必備的沙灘、泥土岸;必須凈化水質;植被多樣性要增加;遊客參觀區和斑鱉繁殖區要分離等。

猶猶豫豫:嫁過來還是招過去?
農業部組織專家修訂的《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擬將斑鱉列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提升保護級別和保護地位。
在具體的保護措施上,專家們提出兩條腿走路——“人工繁殖”和“尋找野外個體”。
“利用現存個體,進行斑鱉的人工繁殖”,這是目前公認的拯救斑鱉最現實的途徑。解焱建議,現存斑鱉的年齡已經不算小,由于現在斑鱉的分散現狀不利于繁殖,希望能將4頭斑鱉集中到一個地方。
5月15日,Kuchling教授再訪中國,和呂順清一起對蘇州動物園、蘇州西園寺和長沙動物園的斑鱉進行身體檢查,並幫助制定具體的繁殖方案。
“我們檢查了所見到的3頭斑鱉,它們的身體狀況都很好。還用了B超,發現有很多卵,最大的卵可能兩三個星期就成熟了。”呂順清介紹說,長沙的斑鱉過去都是在室外的大塘裏冬眠,出蟄後則被抓到特定的小池子供遊人參觀。而蘇州西園寺和蘇州動物園的因為塘很大,不好捕捉,但還是作了近距離仔細觀察。“我們檢查完之後,當場就把檢查結果給動物園和西園寺了,希望他們考慮盡快聯姻。”
但在具體實施上,長沙動物園和蘇州動物園的意見不太一致。
1月底,中國動物園協會曾建議,將長沙斑鱉“嫁”到蘇州,與蘇州的斑鱉結成夫妻,等它們有愛情結晶之後,再將長沙動物園斑鱉調回湖南。
為什麼選擇將長沙斑鱉“嫁往”蘇州?中國動物園協會認為蘇州動物園環境好,斑鱉生存條件好,並且有兩只雄性斑鱉,雌性斑鱉有選擇余地。通過一段時間交往後,它會選擇理想的丈夫。
“恐怕還是蘇州動物園斑鱉來做上門女婿好一點。”長沙動物園管理處黨委書記田建良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電話採訪時如此表示。
田建良解釋,一者,長沙動物園具有50多年的斑鱉養殖經驗,對斑鱉這種淡水龜鱉類的生活習性,飲食起居以及何時產卵、何時冬眠等了如指掌;二者,全世界就只有一只雌性斑鱉,搬來搬去會否影響其健康還得經過專家進一步考察、論證。
“一旦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斑鱉物種就會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我們和蘇州那邊沒有直接聯係過,更談不上達成一定的協議。還是等做好了前期的基礎工作,再作具體的打算。”田建良在電話裏說。
“我們希望長沙斑鱉來我們這兒。我們請了有關方面協調,但對方不太肯。雖然只是兩個單位的協商,但我國行政係統的辦事效率跟想象的是兩回事。”蘇州動物園動物管理部錢先生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
“我們的心情也很迫切,希望盡快拯救這一物種。但是,還應當用科學的方法來操作。”農業部水生野生動植物保護辦公室副處長何建湘沒有正面回答記者關于政府主管部門是否會採取強制性措施的問題。他說,“斑鱉性情兇猛,領地感非常強。因此,從嚴格科學意義上來說,我們要先改造斑鱉馴養繁殖設備設施,讓這幾頭斑鱉有接觸、熟悉的過程,再進行馴養繁殖,以防咬傷甚至致死。目前損失任何一頭斑鱉都是得不償失的。”
呂順清表示,WCS作為國際保護組織,希望兩家動物園能盡快達成協議,為斑鱉的人工繁育提供機會。
在人工繁殖的同時,也不能放棄野外調查。解焱指出,確定現在動物園、個人收藏或被漁民意外捕獲而仍可能存活的未知斑鱉個體也很重要。
還有專家建議,不妨借鑒中華鱘保護的經驗,利用漁政等力量或許會有新的發現,因為斑鱉的捕捉、馴養繁殖、運輸、經營利用等管理權限均集中在省級漁業行政主管部門。
據悉,在斑鱉的分布區太湖、雲南紅河等部分地區,野外尋找斑鱉的計劃已經陸續實施。今年2月,已率先調查了雲南紅河地區,確認1998年雲南省紅河州元陽縣曾放生了一頭斑鱉,這帶來了新的希望——在野外發現新的斑鱉個體仍有可能。
“當前,斑鱉保護財政經費很快就要下達,我們馬上啟動這項工作——馴養繁殖條件改善和斑鱉資源野外調查,以尋找更多的活體,補充斑鱉人工馴養繁殖種群。”何建湘說。
一位網友曾悲觀地在網上留言:“上海動物園斑鱉的逝去,讓我感到,人類對環境的無知帶著自己走向毀滅!”
[相關閱讀]斑鱉的生活習性
每年驚蟄前後,埋身池底淤泥中冬眠的斑鱉開始蘇醒而出。春季的氣溫乍暖還寒,蘇州動物園內的斑鱉只是在陽光和煦的午前浮出水面,緩慢地昂首泅遊,爾後便匍匐在池中的石質小島邊緣,整個鱉體半淹在淺水中,長時間保持靜止的姿勢,酷似一塊小島邊的岩石。通常,被淹在水下的鱉頭每隔2~3分鐘才抬起一次,在呼氣的同時噴射出含在口中的小股水柱,然後張嘴掀鼻進行吸氣,10~15秒鐘後又沉首水中,這樣的呼吸動作周而復始,循環不已。
動物園隔日定時定點給斑鱉喂食。通常飼養員下午兩點于食臺旁用手或木板敲擊水面,在水波震蕩的訊息傳遞下,瘦弱疲憊的斑鱉開始挪動沉重的身軀,離開小島,遊向食臺,攝取投食。斑鱉的進食量與季節、氣溫有關,夏季氣溫高,斑鱉的新陳代謝旺盛,進食量就多,每餐可吞食雞(脯)肉1~1.5千克,但對投喂的雜魚類則嗜食性並不明顯。飽食後常沿著池周漫遊,顯得較為悠閒。此時可見鱉的背部、裙邊、直出的尾巴、輕盈劃水的四肢、前伸的長頸及明亮的眼睛。這樣的遊泳有時可持續1小時左右。該鱉的裙邊雖然清晰可見,但並不豐滿,顯然是與生活環境的水質差、營養條件不理想、健康狀況不佳有關。遊園者常向斑鱉拋擲各種食品,它也樂于容納。盛暑酷熱或氣溫低涼的日子,斑鱉對投食反應比較冷淡,即便來到食臺,也顯得神情呆滯、萎靡不振,毫無食欲,一般在食臺附近遊動兩三個來回後,就沉入水底或返回小島歇息。因此斑鱉在數日或一周內拒不進食的情況屢見不鮮。
蘇州西園寺的放生池面積較為寬闊,水質潔凈,常年保持環流狀態。池中飼養著兩只斑鱉,它們的體質和活動能力,都強于蘇州動物園飼養的斑鱉。它們經常間歇性遊出水面,雙雙結伴而遊,但因池中缺乏小島,只是偶而停息在池畔的假山邊上,稍受驚擾,遂棄岸隱入水下。(見趙肯堂著《瀕臨滅絕的斑鱉》一文)
編輯:姜偉超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